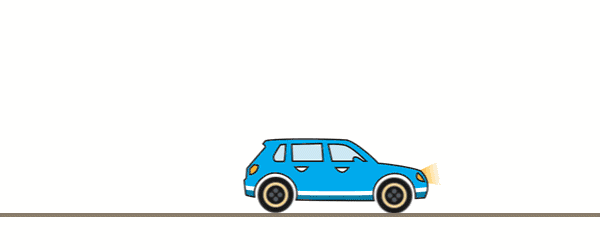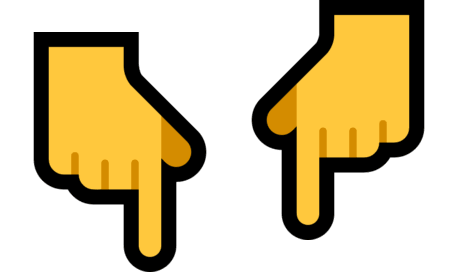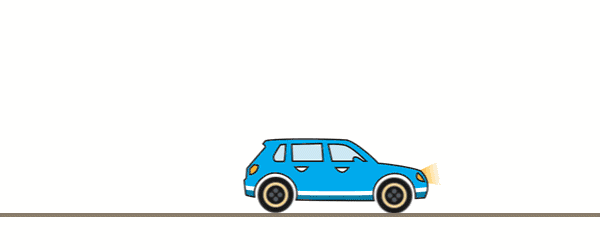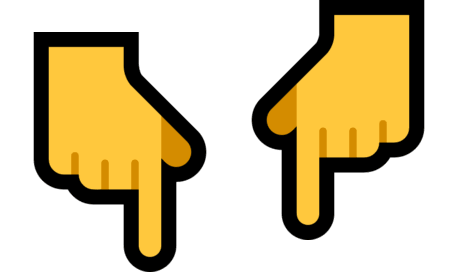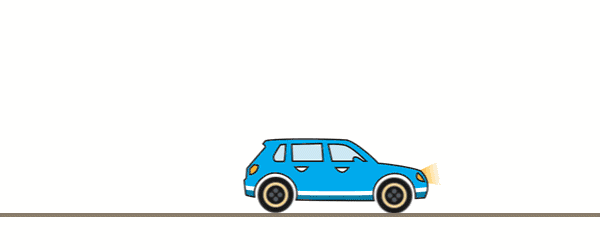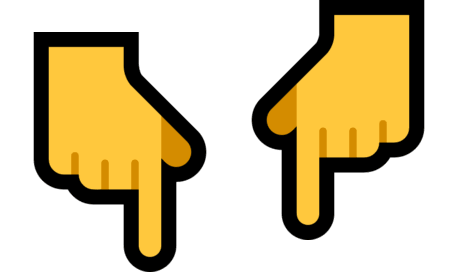我知道一些有关莎拉的趣事。她今年十八岁。在 7月,她以A 等成绩通过生物、化学、物理和英文考试从学校毕业。毕业证书被镶在银色裱框里,和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起放在客厅一角的桌上。按照计划,她本该在9月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但她却选择休学一年为狗狗基金会做志愿者。
空闲时候,莎拉喜欢画名人漫画,和温瑟姆排球队一起打球还有收集泰迪熊玩偶。她也喜欢读奇幻小说。目前,她正读到克里夫·贝克的《编织记忆》第二章的第八节。她最近在和一个叫保罗的男孩约会,尽管她觉得他是个人渣。因为保罗不愿意和胸大且风骚的“极品荡妇”汉娜撇清关系。这让莎拉相当恐慌,但她无法向她的母亲倾诉,因为她觉得母亲一定无法理解,并且很可能会像上次一样情绪失控。于是她把这些告诉了艾丽卡,由于年长一两岁的缘故,艾丽卡要更加聪明和世故。同样,莎拉也没和她母亲提起过艾丽卡。
莎拉卧室的四面墙都被涂成了淡紫色,透过涂料,还依稀能看见原来老墙纸的花纹。她的单人床上盖着白色的被罩。她习惯把衣服和湿毛巾都丢在地上。她的架子和梳妆台上塞满了动物玩偶。用传统工艺制作的长毛绒熊是她的主要藏品,每一只的标签都完好无损。要弄清这些熊的数量实在太浪费时间,但我还是要说,一共六十七只。
那天早上,莎拉花了不到半个小时洗澡,又花了五分钟出头的时间刷牙。她没有龋齿也没补过牙,不过由于过度清洗,她上门牙的牙釉已经开始变薄了。她同样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上涂上了牙膏,为清洁牙垢做徒劳的努力。她家里没有烟灰缸,她把香烟和打火机藏在梳妆台中间抽屈内一双卷好的裤袜里。
第二天是莎拉的生日。很多人寄来了生日贺卡,它们整齐地排列在客厅的壁炉台上。今天早些时候已经有人来打扫过了,但现在咖啡桌上又多了一个空的马克杯和一本《热度》杂志。不管看不看电视,莎拉都习惯把它开着。
我同样发现,她做了比基尼线脱毛。她大部分的衣服是绿色的。她梦想去澳洲旅行。她有驾照却没有车。她最后看的 DVD是《吸血鬼猎人巴菲》——同名电影而不是那部更知名的剧集。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她的猫也叫巴菲。
幸运的是,厨房地板铺的是赤陶瓷砖,并且我很快找到了放着拖把、桶、漂白剂、抹布、一卷垃圾袋和很多抗菌喷雾剂的清洁柜。我没计划在这里做这件事,我有一千零一件其他的事要做却没有时间做。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不小心划破她的动脉惹出的麻烦。还好我反应够快,大多数的血渍都没溅到墙上。
为了方便运输,我用一把十四英寸长的锯锯下她的四肢,再截成两段,从而轻而易举地把她的手臂、小腿、头和一些在她企图逃跑时挣扎掉下的头发一起装在了一个垃圾袋里。臀部和大腿则装在另外一个袋子里。我把它们放在后门边,离血摊远远的。尽管莎拉身材瘦小,她的躯干还是异常沉重。装她需要一个能负荷重物的橡胶袋,以防止破裂或渗漏。还好我周全地随身携带了一个。
清洁过程相对容易。我把衣服装进手提袋里,并在洗手池里洗了脸。滴露喷雾和温水足够清洗干净橱柜门上溅到的血迹,也能在我把大部分血抹到地上后清理干净橱柜操作台和饭桌。清理地板用了三桶稀释过的漂白水,最后都排到后院的下水道了。水槽的垃圾处理器用来处理碎肉。水池是不锈钢材质的,只需要事后随便擦一下就好了。
我唯一的顾虑是早餐桌上的一些小划痕,是我不小心用刻刀弄出来的。有一两滴血渗进了木头里,不过不怎么看得出来,再加上桌子本身也比较旧了,人们不太可能发现血迹。总的来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曾来过这里。
事实上,在我把垃圾袋丢到花园,把妈妈的东西放回原位后唯一没法处置的东西就是我自己了。幸运的是,莎拉父亲和我的体型差不多,我从他的衣柜里翻出一条浅褐色长裤和一件橄榄绿的针织衫。尽管针织衫的肘部磨坏了,闻起来也有一股霉味,但它干燥并没有沾染血渍这两点对我来说更重要。
我满足地穿上自己的夹克和鞋子,走出房间并轻轻关上了身后的门。
阿伯特的家遵循着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用一条花园小径把自已和邻居家隔开。每个花园都围起高耸且压抑的防护栏,底部用普通砖墙加固,象征性地保护一下隐私。考虑到这堵墙比我高六英尺并且我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把莎拉一起扛过去,我决定先取车再回来处理她。
我助跑了一段,翻过栅栏,落在了一堆嫩枝和柔软的棕色树叶上。栅栏地基几步远之外就没有树了,旁边是陡峭的斜坡。我就是从这里看到楼上的玻璃渐渐升起雾气,听到浴室的水声,看到莎拉脱衣服的剪影,并等到她关上门,耳里只能听到流水声的时候才溜进去的。现在当我穿过成排的松树走向路边,这里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光景了。那些让黎明显得完美的一切都消失了一房顶上的小堆积雪,鹿蹄下树叶发出微弱的嘎吱声,好奇的狐狸穿过树林发出的沙沙声。如今取代它们的是柴油引擎的咔哒声,水泥搅拌机轰隆作响,早餐时段广播的白噪声,和砌砖用的小铲子发出的哒哒声。这种变化是我来后不久开始的。尽管工程完成后可能会带来美好的宁静气氛和友爱的邻里关系,但目前这无法避免的噪声使这个混乱的郊区变成一个活地狱。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喧杂让我不必偷偷摸摸地行动。
想到这些,我意识到好像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被漏掉了——我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走路时我已经习惯有一种重量压在我的腿上,然而现在这种习惯带来的舒适荡然无存了。
直到走到货车旁边我才发现我把那见鬼的钥匙锁在屋子里了。
我本不想打破窗户的,但是我的福特全顺启用了加固双重校验锁。并且我在订购它时特别申明要安装上额外的全副警报系统,这样的结果是: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也很难进入车内。现在坐出租车回去取备用钥匙时间太紧张,权衡了各种选择后,我很快找到了一块砖头。尽管这需要以牺牲暖气为代价,我还是继续这么做了。
我把莎拉留在侧门旁,自已从两车车道绕过去以减少被发现的可能。我花了一点时间再三检查房子后面厕所的小窗户,窗户被我碰掉了一些油漆,木头上看得到明显的凹痕,但它是关着的,并且玻璃完好无损。从里面堆积的箱子和毯子的数量以及布满的蜘蛛网可以看出,这些破坏在夏天前都不会被发现了。很好。
我很高兴莎拉并没有从任何一个袋子里滑出来。把一些稍轻的袋子装上车花了我一点时间。但当我返回去拿橡皮袋的时候,我碰巧瞥了门口一眼,心头一震。充满疑感地看着我的是一个熟悉的面孔。我曾在一个商场快照机照出来的小相片里稍微端详过这张脸。照片是在我把莎拉的日记本摊在她床上时掉出来的。确切无误。
艾丽卡满是犹豫地站在那儿,我几乎能听到她脑子里嗡嗡作响的声音。她的手指指向门铃,目瞪口呆。我完全明白她脑子里现在想的是什么,所以我微笑并友好地挥手来转移她的思绪。
她立马换成了抱歉的语气:“不不,我没这么想。”她笑了垂下的几缕发丝遮住了她的眼睛。
“老年关怀中心,”我解释道,“只是来收一些旧的袋子。哈哈!”
我指的是装着旧衣服的袋子,你是来找那位年轻姑娘的吗?
她正在走向我。深色的卷发晃动着,羊毛围巾随着她臀部扭动的节奏起伏。伴随着她每一步自信的步伐,她的乳房都快要把她外套最上面的那颗扣子挤掉了。
我血管里的血液开始加速流动,机械挖掘机和风钻的噪声慢慢变轻。“对,你知道她在哪儿吗?她没有应门。”我和她之间的距离近到我可以听到她大腿间牛仔裤摩擦的声音。我可以用很多方式解决现在的处境,但是像我通常遇到绝色美人时一样,我的诚实迫使我先发制人。
“是的,”我说,“她在花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