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祝善知识大菩萨 智慧为体慈悲是用 知幻无苦大爱度世

▼今日份音乐

【我们都喜欢性爱。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或神明,离我们十万八千里,也不是地狱或粪蛆,并不邪恶和污秽。它与我们面对面,触手可及,是吸引我们要去的温暖、隐秘之所,我们在那里寻求抚慰和极乐。可惜,它又常常逃避我们,令我们撕裂。或者伪装成怪物,令我们羞愧不堪,自我折磨。这不是它的错。是我们有毒,是我们中毒了,是空气被恶毒所污染。】

安宁的身材瘦削一些,脸蛋儿是鹅蛋型,在我记忆里,她的脸上总有一、两颗痘儿。
安宁不爱说话,很安静,她的眼睛看你时,仿佛自己保守了一个秘密,永远不会对你说,但也永远不会对你有任何恶意。
她不但对任何人没有恶意,还克制着对所有人的善意,她顺从这个世界,同时又对这种顺从的姿态保持克制,不让这种姿态过于明显。
安宁眉目清秀,皮肤白皙,她的肩窄窄的,双手总是垂下来贴紧双腿,她的腿长而直,长大后一定会令我们这样的男性升起不纯洁的欲望。
安宁经常让我想起我的哥哥,村里人总说哥哥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他像的那个女孩子应该就是安宁。
应该让10岁的哥哥和9岁的安宁结婚。当我回忆安宁时,脑海中就出现了一对儿童的结婚照,照片儿的颜色就像现在你正在阅读的字体的颜色,两个小孩儿像两根挂着露水的小葱儿,笔直、认真地站在泛黄的照片儿里。
如果安宁和哥哥结婚,我一点都不会难过,因为我喜欢的是娜宁。
37年前的娜宁比安宁还好看、活泼,她脸上没有痘痘,咧开嘴笑的时候,脸蛋儿比姐姐的还要大。一想起她那么漂亮,现在的我都想回去亲亲那个小娜宁的嘴巴。你会发现,娜宁的嘴唇、酒窝儿、头发卷儿和衣服,浑身上下,都有一股好闻的奶香味儿。
如果再有一对小孩儿结婚,就是娜宁和我。那时我6岁,娜宁5岁。但我生日小,娜宁的生日大。娜宁的生日超级大,像一颗剥了皮的煮鸡蛋那么大。
娜宁是高贵的天使,而我什么都不是,连一颗狗屎、甚至鼻屎都算不上。尽管如此,娜宁和我结婚,是再适合不过的事儿。

安宁和娜宁都不是我们村的人,她们从东北方向跋山涉水来到这里,中途有2.5公里的土路。她们到她们的姑妈家做客,我和哥哥就认识她俩了。
情况应该是这样。
安宁和娜宁应该是真实的存在。
我的记忆应该没任何问题。
有时候我对自己说,你总不可能编造一个完全虚幻的故事,兴师动众,涉及很多现实里的人,仅仅是为了欺骗自己。
但说实话,我很少有机会跟哥哥或者其他任何什么亲人、朋友,或者有共同记忆的人,去怀旧和探讨自己儿时的故事。
由于年代久远,缺少交流和佐证,我对自己早年经验的回忆,总是虚虚实实,如梦如幻,令我缺乏信心,我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患上了妄想症。
我和娜宁,哥哥和安宁,我们四个,应该有不止一次共同玩耍,谁知道呢,上帝也许都记不清了。
冬天的一天,姑妈牵着安宁和娜宁来我们村玩的时候,天空阴沉,空中飘着大雪,西北风把雪花吹成了斜线,把天空也吹成了一绺一绺倾斜着的灰蓝的东西。
好冷。
我看见一个箍着红头巾的女人,拉着两个漂亮的小姑娘,从穿村主道由东向西走来,匆匆忙忙,一晃,就消失在了她家的门洞里。
“娜宁和姐姐又来姑妈家做客啦!”
当时我高兴地放了一个屁,差点儿没拉进裤裆里。
第二天,大地上覆盖了一层白雪,天气放晴,阳光照耀白雪,白色的光晕笼罩了整个世界,一切都像梦那样美好。
我一定是色迷心窍了。
“娜宁,我们到对面河岸上去吧。你看,那里有座山(土堆),我们到那座山上去,再回头看,就能看到你姑妈做什么好吃的……”
“可以,不过,雪太厚了。”
“来,我拉着你的手。”
我和娜宁就这样手牵手蹒跚着,越走越远。
当时娜宁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身子圆圆的,她的脸蛋儿那么好看。我抓着娜宁的小手,感觉到它的温暖、柔软和光滑,令我不安而又陶醉,就像长大后每个男性都喜欢的那种小东西。
(不知道哥哥和安宁到哪里去了……)
当我从冰窟把娜宁举上冰面、自己却爬不出来的时候,只能将胳膊尽力搭在冰的边缘,等待死亡把我拖下水。
娜宁飞快地跑回村子,叫来了救我的人。
这就是整个故事,非常简单,但我的记忆却十分模糊,后来我问过哥哥一次。哥哥说,有一回,不记得几岁,确实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你可能差点淹死或者冻死,但具体什么情况,我一直不太清楚。
“很奇怪,你记得那么小的时候的事,我小时候的记忆全部消失了,现在只能记住昨天的事,前天的事就都忘了。”
哥哥对这样我说。
到现在我仍会怀疑冰窟求生的事是不是自己的杜撰,至于我是否拿这件事问过哥哥,我也记不清了,因为似乎这询问也发生在若干年前。
不知从何时起,或许从生下来开始,我就不太跟父亲和母亲交流了。
后来许多年,我只一遍又一遍用回忆、设计、推理和自我重复,来构画和填充自己的成长。

再次出现安宁和娜宁的记忆,大约是冰窟事件的四年后了。
那时我已经10岁。
那天上午母亲一边哭泣,一边拉着我的手,穿过村子的十字路口。我突然看见安宁和娜宁姐妹两个,正站在姑妈家的大门口,看着我。她们已经亭亭玉立了。
我和她俩,对于彼此的突然出现都感到有些意外。我想叫她俩的名字,但终究没有叫出口。母亲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她只是用力拉了我一下,继续向前走,去她要去的地方。
安宁和娜宁似乎也要叫我,但没有叫出来。她们的表情中应该有意外、惊喜和困惑,或许还有难以言喻的感伤。她俩穿着崭新的裤子,裤子是米黄色的。安宁的裤脚上绣着一只不大的梅花鹿,娜宁的裤脚上绣着一张圆圆的花猫脸。
上午的阳光照着姐妹俩柔嫩光泽的面庞,照着她俩的新裤子。安宁右手搭着娜宁的右肩,左手被娜宁的双手攥住。她姐妹两个就像两个美丽的天使,站在上午的阳光里,与我对视了三秒钟。
我扭过头,看见母亲懦弱的哭泣,踉踉跄跄,被母亲带走了。
自始至终,母亲都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
这次晨光中的偶遇,我们的童年都已接近尾声,但我仍不确定,它是否发生过。这可能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机会,同时见到她们姐妹俩。

时间的容量特别神奇。有的人一辈子平平淡淡,一眨眼就过去了,有的人十年、十个月、十天,可能要经历别人十辈子的事。
只要我一张嘴,敲几下键盘,十三年就过去了,我就能从10岁,变成23岁。
但这十三年我经历过什么,我不会告诉你。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任何必要。重要的是,就在我已经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忘记娜宁和安宁这对神仙姐妹、幼时玩伴的时候,娜宁再次出现了。
一个冬天黄昏的时候,我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东西,回家时路过十字路口,我看见娜宁孤身一人,站在姑妈家门口。她当时的身影,像一剂永远无法释解的毒药,就这样住进我生命的记忆。
我甚至没有看清她的相貌。
我不得不说一句,那时我23岁,娜宁22岁,我们已经有十几年没见面了。
尽管黄昏的天色隔开了我和娜宁,但我仍然愿意欺骗自己——说我看到了娜宁的美。
就像我突然就不是自己了,同样,娜宁突然就不是从前那个小娜宁了。
眼前的这个女性身高已经翻倍,体态丰满,尽管一些线条显得笨拙,但身体上的任何一条曲线,都确定是曲线。
她的脸庞轮廓丰满,却显出棱角,面色在昏暗下泛着微光,眼睛也不像小娜宁那样柔弱、游移而空灵了。她的黑眼珠闪耀着紧张的光芒,不知道是急于吞噬还是急于喷射,漆黑如夜,仿佛随时有泪水溢出。
娜宁的美,首次以隐晦的性感和突兀的焦灼,进入我的记忆。这种进入,再次强化了我的生命如幻之感。在那之后的二十年,我都久久不能释怀。
娜宁的一切,正是我整个生命想要的。奇怪的是,有关她的一切,似乎都是我幻想出来的。
她年轻炙热的身体,痛苦焦灼的目光,像深渊一样的生命经历,似乎都只能用我一生的情绪和想象来创造和填充。
娜宁和我之间,被生命隔开了,被永恒隔开了。
她在黄昏里看见一个年轻男子匆匆走过漫长的尘埃,一闪而过。他看了她一眼,慌慌张张扭过头去,继续走进他的迷雾,犹如这眼前初冬的昏色,而对她生命的求救,选择视而不见。(他也在向谁求救。)
娜宁的整个身体和全部肌肤都在膨胀,僵硬而笨拙,揭示着生命发育时的愚蠢和痛苦。她的面庞性感得如同埃及艳后,直到现在,我才留意到她的头发,是天然卷曲的,吻着她的额头、太阳穴和脸颊。
我回到家,只有年迈的外祖母坐在蜡烛的光晕里。(停电了。)她紧闭嘴巴,下巴抵住前胸,正盯着自己十指交叉、放在肚腹上的双手,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心事。
当我询问的时候,外祖母告诉我:“是的,你文婶娘家是有两个侄女,她们小时候经常来我们村。”
外祖母的话证明我没有患妄想症,而且几十年一直没有患什么妄想症。

25岁,我大学毕业了。偶然一次去文婶家,也许不是偶然,是瞥见了谁的身影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去的,总之,我在文婶家遇到了安宁。
是安宁,不是娜宁。娜宁不在。
让我算一下,那时安宁28岁。
安宁仍然清秀,但她的身高还没有记忆中两年前的娜宁高。安宁也没有娜宁漂亮,尽管还算耐看。她仍然温柔寡言。
安宁和文婶一起坐在矮桌前包饺子,我胆怯地坐在边上,强行装作随意,不着边际地跟娘儿俩叙旧。
最后,我要到了娜宁的电话。
(听说娜宁在北京生活?已经结婚了?什么时候结的婚?)
后来,那年冬天,我去了北京,在北京做了很多工种,文员,工业设计,电话销售,保安,诸如此类。
到了第二年冬天,我已开始在大兴做保安了。
集训的时候,大队长对我大学本科的学历感到惊奇,他奇怪的是,一个大学生为什么要来当保安。
他感到奇怪,我自己并不奇怪。
我在保安队认识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上的人,这些人和经历都很有趣,但偏离了娜宁和“性爱”的主题,以后有机会再记述。
我关注的是在寒冬腊月值夜班,一个人或两个人,坐在窄小的保安亭里,不能睡觉,因为可能有人到飞机修理厂附近偷东西。
那时候外面又在下大雪,窗子黑洞洞的,保安亭里电暖气开得很热,结伴值班的坏小子睡着了,我不困时,就看着外面的雪花,在空旷的黑暗里簌簌飘落,给娜宁发手机短信。
娜宁说她结婚了,她嫁给了一个东北人。
她还说过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我给她发过不多不少的信息吧,内容和情感都应该比较克制,也应该抄录在日记本上了,但近二十年前的日记本子,必然不在手边,锁在老家的箱子里。
我特别记得27岁时的情人节,我们有过短信通信,她应该对我说过温暖的话,比普通朋友更温暖一些。然而,也只能这样。
那时候她已经结婚一、两年了。
我还没有交过女朋友。
我会幻想娜宁的东北丈夫如何粗俗和粗暴,娜宁并不幸福。
今天想来,我真可怜。
我好像一直都很可怜。
写到这里我就想笑,当然,不知道笑什么。

对于我的性爱史,关于娜宁,我只能写到这样。也许到下一篇的时候,我的写作水平就会有提高。
到现在为止,我都不能确定我认识娜宁。但娜宁确实存在,她确实是贯穿我一生记忆的梦幻。我和娜宁之间的距离,不过是命运和命运之间的距离罢了。
并不遥远。

关注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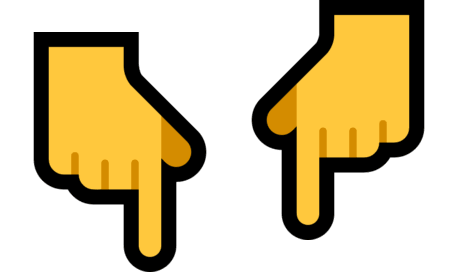
读 原 创 因 缘 不 易 点 赞 转 发 大 布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