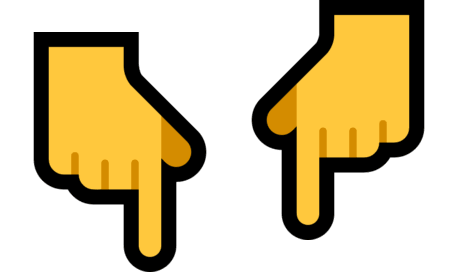让我们再多谈谈“不做”。佛说过一段著名的有关“心”的话:“心。心无。心是明。”它被到处引用,学者们为此还写了好多书。这段话的第一句是“心”,这个字引出了佛初转法轮的所有教授,也是当今佛教徒与科学家感兴趣的话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对“心”的定义,突破这一点之后就没问题了。佛的话没有随意说的,也没有只是为方便而说的。不过即便我们这些唯物主义者,特别是科学家,也常说:“我的心知道它。”同时我们又把心视为假设,只不过是加在大脑功能或遗传功能上的一个标签。
在古印度,出现过一些令人赞叹的思想,商羯罗(Shankara)、玛哈维拉(Mahavira)、佛陀,是其中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两千五百年前,这些哲学家就在怀疑“心”是否存在!不过,佛的这句被称作“狮子吼”的宣告,是以“心”这个字开始的,表示心是真实的。所以如果我们问谁在做“不做”?答案是:心在做“不做”。
这段话的第二句是:“心无。”佛否定了自己的第一个陈述——“心”。让我们想象一下,当人们开始专注于佛说心存在是个事实时,佛又说没有心。佛二转法轮的所有教授即来自这第二句话。现在如果我们问,谁在做“不做”?答案是: 没有心在做“不做”,也没有什么叫“不做”。
这句名言的第三句也即最后一句是:“心是明。”你看,佛又推翻了自己的前一个表述。“明”,就是佛性的另一个名称。如果我们再来问,谁在做“不做”?答案是:“明”在做这个“不做”!
为什么佛要说:“心。心无。心是明。”为什么佛要在一段简单的话里说三件事?为什么不只说一件事?因为他意在破除三种邪见。第一,佛要破除恶的念头、态度和行为,所以佛说有心。依据我们的行为表现,心会入地狱、天堂或饿鬼道。第二,佛要破除心是真实存在的见地。第三,佛要破除所有见地,因此佛不仅破除心的存在,也破除心的不存在。
我们之中有些人会怀疑,能否把正在讨论的内容用于实修。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部经在说什么,有些人理解一点点,甚或只是一两个字,而理解的这一点点,我们也把它看作纯粹的理念,也许在逻辑上有道理,但也只是对读诵和思考有用,仅此而已,我们看不出如何把这部经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有些人相信,读诵经文,把这部经供在佛堂上,会得到加持,但我们理解的“加持”,依赖于某种超自然的、无法言传的外在之物,这使它基本上成为一种很细微的有神论方法。
我们如何能什么都“不做”? 这是很值得一问的问题。从一开始,甚至“不做”本身己是一种做。我们现在能做的最接近“不做”的事,就是禅定。当我说禅定,那不是指观想和放光、收光。虽然这类的方法是存在的,不过这些好的和深奥的方法,只是训练我们心的其他方式。
说到禅定,大多数人想到的是:保持安静,不说话,坐直,闭上眼睛,盘起腿,诸如此类。可是这些理解只是禅定的外相。对许多人来说,禅定还意味着获得控制自心的能力。我理解为何有人会这样想象禅定。当我们教授禅定时,别无选择地说:“不要受干扰,专注。”因此让人觉得它与控制自心有关。但这也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如果控制自心就是禅定,那么严格来说我们一直在禅定,因为我们的心始终受到某些外在对象的控制,比如赞美、批评、权力、金钱,凡此种种。举例来说,当我们悠闲地阅读八卦专栏,我们就在试着以八卦新闻控制心。为了娱乐,我们都这么做。对有些人来说,娱乐是去看电影;对有些人来说,娱乐是坐在佛龛前,闭上眼睛念咒。不过,依据佛陀的教法,八卦、电影或念咒,都不能令我们直接经验到“不做”,要去经验它,我们得试些别的。
不幸的是,我不得不说,虽然禅定确实与坐直有关,可是坐直与能不能成佛无关。如果坐直在达到证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什么我们不干脆把脊柱焊直?那样我们无须专注,身体都会保持挺直。然而我不得不说:“只要坐直,不要观想,不用念咒,别无其他。”另外我还得说:“不要做白日梦。”
我们经常做白日梦,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心就被白日梦占据了,心在忙碌。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从白日梦里得到好处的方法。不过如果我们真能从中找到赚钱的方法,那可能会耗尽白日梦的资源。不做白日梦意味着,不忆念过去,不想象未来,完全安住当下。
像“安住当下”这样的话,非常有欺骗性,容易导致误解。一旦我们的老师说“安住当下”,每个人就像是鱼竿上装了鱼饵的钓钩那样,去寻找当下,然后等上整整一天,直到当下来上钩。我们就是这样等待当下的。其实当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而我们却在等它。寻找当下不只是件可笑的事,还是件蠢事,不是吗?还有什么比这更蠢的呢?你不要去找它,它就在那儿,无处不在,谁会错过它呢?
有些人比这还笨,笨到真的找到一个“当下”,还在写给上师的浪漫报告里吹嘘它。如果我们真正客观地面对它,这样的发现又有什么可夸耀的呢?又不是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稀有物种。
大多数时候,禅定者找到的所谓“当下”,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当下,它只是禅定者描画出的不真实的当下。找到真正的当下就如同遇到某个人,他具有的特质我们自己已经发展成熟,所以我们丝毫不感到讶异。对于真正找到当下的人来说,没什么好报告的。如果现在我说从我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很多头,这会令你惊讶吗?有什么可报告的呢? 这就是为什么佛在《金刚经》中说:“当燃灯佛授记我将证得菩提的诸种功德时,其实意味着,无菩提功德可证。”假使老师说,这个房间里有个人有金色的脑袋,我们的心就会描画出一个长着金色脑袋的人,然后在这房间里到处寻找。不过这里当然没有人长了金色的头,因为没有,我们就报告老师,没有找到金色的脑袋,但是这没什么可炫耀的。反之,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一个金色的头,那就更糟糕了,因为你找到的是你主观上想寻找的东西。
安住当下基本上是说,无论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安住在那上面,只是与它共处。如果此时此刻,在这个讨论《金刚经》的神圣场合,你们有人碰巧想要强暴一头大象,你不应该想:“哦,我是个佛教徒,我怎么能想到强暴,更不用说强暴大象了!”我们会这样想!当然,这样的想法大多又要归功于孔老夫子及佛教大师们,我们被彻底洗脑了。如果我们认为,不应该想到强暴大象,或者我们觉得强暴一只苍蝇可能感觉好些,因为它比较小,这些想法都是我们从诸如衡量等社会常规中学到的复杂性。
我们理当安住在心中生起的任何念头上,丝毫不带判断地看着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有比噩梦中的大象还糟的——好的念头更加糟糕。比如在这个神圣的时刻,突然我们想要拯救整个世界,然后我们就自夸说:“时至今日,我所有的佛法修持总算都有了回报。啊,这是诸佛和上师们的加持,我终于有了些真正的慈悲心!”之后我们的心上蹿下跳,试图去完好无损地保住这个念头,担心它溜掉。我们珍藏它,想把它锁在某个安全的地方。不过再一次地,我们没有在禅定。现在,让我们坐直一分钟左右,看着我们的念头,包括大象……
我们可能会问:“禅定会让我们成佛吗?”答案是:“是的,它会。”不只是我这样说,过去的诸佛、学者和圣人,也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是的,这可以把我们从所有的迷惑中解脱出来。”《心经》和《金刚经》说:无可禅修,无得,不增,不减……可是我们很难相信它。为什么这么难?因为它太简单了。在我们心里,唯一能成佛的方法是念十万遍咒语,或者修建一座寺庙或一所医院。不过,如果一个人每天只是修习这个简单的禅定,即使我们不想要慈悲,当我们的心离于判断的时候,慈悲就来了,这就是慈悲;即使我们不想要智慧,当我们的心离于判断的时候,智慧就来了。当完全住于当下,我们就什么也没做,也没有在改变,没有在大象和苍蝇之间做选择。
顺便说一下,如果我们正跟大象搞在一起,在欲望还没彻底满足之前,来了一只苍蝇,我们这样的禅定者可能会想“不行,我得先跟大象结束。”这不好,不用这么想,还有很多大象呢。而且如果你忽视它,这只大象也不会伤心的。所以如果你的心在巴黎,就让它在巴黎,不过你并不需要想完整个巴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