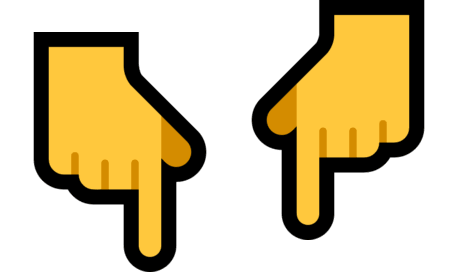佛法的参照点永远是某件事情是否更接近实相真理,因此,任何带你更接近实相的,就是福德,任何带你远离实相的,就是缺乏福德。
我想借这个跟大家谈话的机会,为自己累积一些福德资粮,很感谢摩诃菩提会(Mahabodhi Society)提供这样的机会。在许多关于“大菩提”(Maha Bodhi) 的解释中,我想最普遍的诠释是“伟大的心”。在这非常强调物质主义的末法时期,尤其是在硅谷这样的地方,我想我们应该借这次机会,认真地谈谈什么是“伟大的心”。或者暂且别谈“伟大的心”,在我们这个时代,甚至对“心”的讨论都还不够,因此我们没能善用我们的心。即使我们真的在心性上下功夫,也总是与物质主义有关。
举例来说,我们今晚要讨论“福德”,可是在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不喜欢谈福德,而喜欢谈“运气”。运气与福德,至少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二者截然不同。就我所听到的,当人们谈到运气,那好像是某种偶发的、与因缘无关的东西。假如你真正相信科学,你就不太可能真正相信运气;同样的,如果你是佛陀的追随者,我想你也不太可能接受大家对运气的诠释。因此运气应该只是人们彼此用来祝福的话:“祝你好运!”
我接受的训练使我了解到,我们其实不可能让运气偶然发生——我们既没有生产运气的工厂,也没有教我们如何创造运气的书籍。运气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上的哪个年代,运气似乎都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特别的角色。我听说有些文化使用大蒜串成的花环来增加好运,而别的文化却用这同样的东西来驱魔或赶走厄运。很有意思的是,大家都认同不能真的去创造运气,但同时又会互赠一些荒谬的东西以带来好运。比如有人说:“这会带来好运!”然后给你代表好运的一分钱,可是你不能拿这一分钱去买任何东西。又或者他们会给你一根羽毛、一片树叶,诸如此类的东西。
如佛所说,诸法因缘生,而“缘”不外乎就是你的心,但我们有时对无法确指的运气太过认真。我发现在台湾有些高楼没有第四层和第十三层,听说是因为这些数字很不吉利。那么其他文化又怎么看呢?如果你开始在意每个人对数字的不安感,可能到最后什么数字都不能使用。
不过虽然我这么说,其实我自己也会被坏预兆影响。比如通常我去看父亲时,他会不断地责骂我,今早我刚从父亲那里离开,可是这次他完全没有骂我。你们要了解,我把父亲视为至少是一位很有证量的修行者,当他责骂我时,我认为那净除了我的许多障碍,但这次他没骂我,让我感觉很不安。总之,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是要让你们对运气有一些大略的认识,然后你们才会了解,佛教所谓的“福德”或藏文所说的“康亚”或“索南”,其实与“运气”的概念并不相同。
我要跟你们说一个我刚刚想起的故事,西藏德格有过一个小王国,这个皇室的血脉在大约一个世代以前中断了,现在已经没有德格皇室的后裔。大家都相信德格一位非常重要的国王,曾是伟大的西藏上师蒋扬钦哲旺波的弟子。曾有预言说,当他们两人举办大法会时,蒋扬钦哲旺波应该在法会上把德格王痛打一顿,如此德格王室才能持续传承下去。于是甚至时至今日德格人还会说,由于德格人没有福报,所以法会那一天德格王的表现好到蒋扬钦哲旺波找不到打他的理由。
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个故事,是因为这是了解福德的另一种方式。福德的概念是非常广大的。在佛教的某些派别里,比如声闻乘,他们没有大乘佛教徒关于佛性的概念,他们只谈福德。而我发现,有关福德的诠释混杂了许多文化上的认知。曾有人问我:“累积福德不是很自私吗?”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作为佛陀的追随者,我们难道不应该去除对任何事物的执着吗?我们怎么会有积聚、储存存款这类的心态?我们怎么能够投资福德?在讨论这些问题以前,让我们先谈谈福德的重要性、它的功能以及它的作用。
福德,或藏文的“康亚”,只是个名称、标签。刚才我提到,许多人认为运气只是必然会发生的偶然事件,但福德不是这样。福德的道理,其实是业力原则最高且最细微的面向之一。业力通常要比空性难教,概括地说,“业”就是因、缘、果。举例来说,如果你种花,一旦种子、肥料土壤、水分、时间和空间等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块儿,又没有任何障碍,花一定会绽放。在这种层次上了解因果还算容易,不过,一旦涉及了某些隐含的因素就比较复杂了。譬如用同样种类的十粒种子种花,当其中一粒种子表现得不太一样时,我们就必须更深入地探究,为什么对这些种子的照顾完全相同,可是这粒种子的表现就是不一样?因此你可能猜想,也许是某个特殊事件影响了前二代种子的基因。当我们开始探索更多的隐藏因素,有些人就会从此变成宿命论者,还有些人则变成虚无主义者、科学家、有神论者、无神论者等各种论者。
接下来的一点各位要特别注意: 根据佛教理论,福德是可以由你去创造、捏造积聚的东西。假设你有两个小孩,一个很懒惰,书又念不好,家事也不行。另一个则恰恰相反。可是他们长大后,你不抱任何希望的那个懒孩子,却比较成功。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如果你问佛教徒,他们会说这是福德使然;或者他们可能首先会说,这是业力的缘故。这么说有点危险,因为许多人接着会想:“所以这就是我的命吗?我不能改变它吗?”很多时候当人们听到佛教徒对“业”的诠释,他们的想法通常是这样。所以假设某人有六个鼻子,你不能说:“他无法摆脱有六个鼻子的业。”这不是佛教徒对“业”的诠释。业力不是要这个人不断地想:“我摆脱不了这六个鼻子,我改变不了这种情况。”“业”是可以自己创造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譬如,如果你想再多要一个鼻子,你可以做整形手术——尤其如果七还是个幸运数字的话!了解“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再讲复杂一点。有个东西我们称之为“共业”,或者“共同的福德”。举例来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因为有何种福德还是因为没有何种福德,所以某一位总统候选人会当选。身为世界的公民与另一个国家的公民,我很关心这件事,因为我还是认为,美国总统在这世界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连非美国人,也需有足够的福德才能让美国选出一个好总统。
当我们讲到福德,我们讨论的对象不单是一些重大事件,也可能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俗事。福德完全是相对的。譬如说,你开车去某个地方并顺利抵达,可是你到处都找不到停车位。假设你是去赴一场美妙的约会,结果只因为找不到停车位而把一切都毁了,这就是缺乏福德;但假设你因为找不到停车位,正开车到处转的时候,你本来要进去的那栋大楼突然坍塌了,这就是有福德。
福德确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经济、政治、世俗生活,甚至说话的语调,从许多方面来看,它都是非常相对的。我们也许可以说,因为我们现代人拥有好的福德,所以我们有iPhone这样的手机,不必走老远的路去跟某人讲话,只要打个电话就行了。不过换一个观点来看——像密勒日巴那样的人应该会同意这个观点——正因为我们缺乏福德,所以才生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拿我来说,我总不记得明天要做什么,所以我得要我的iPhone才行,所有事情都记在里面,它就像我的第二个脑袋一其实是第一个脑袋,我头上的这个才是第二个。